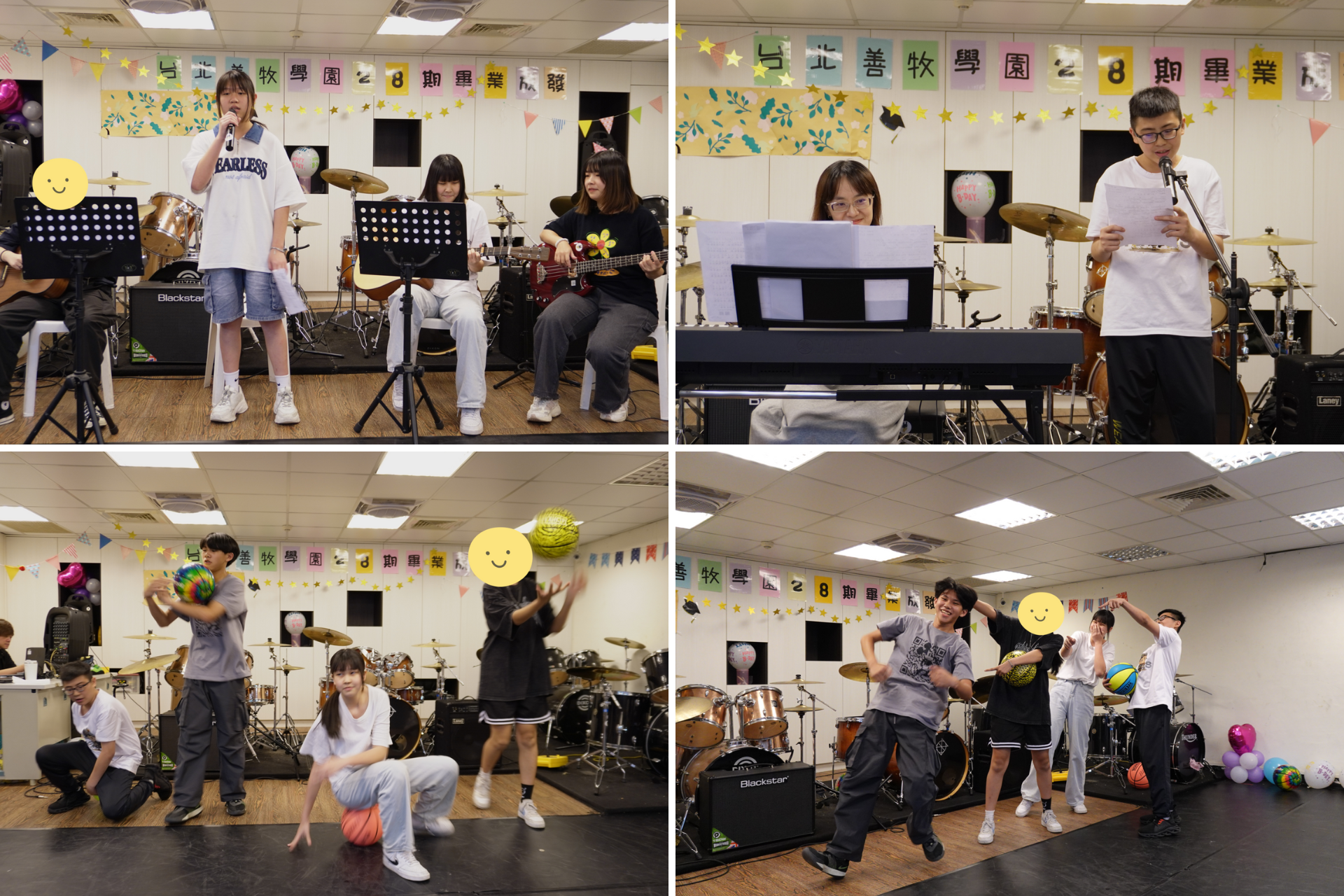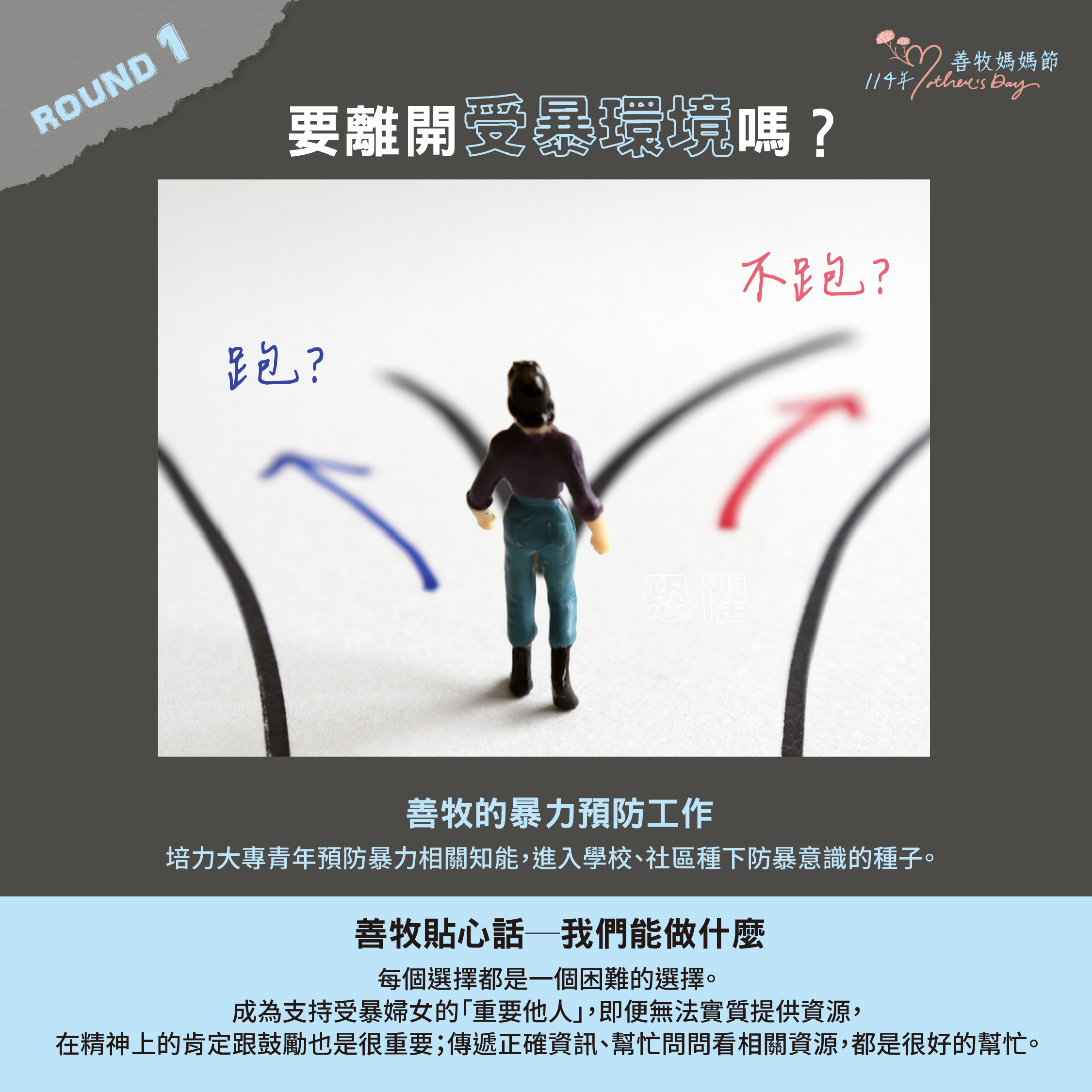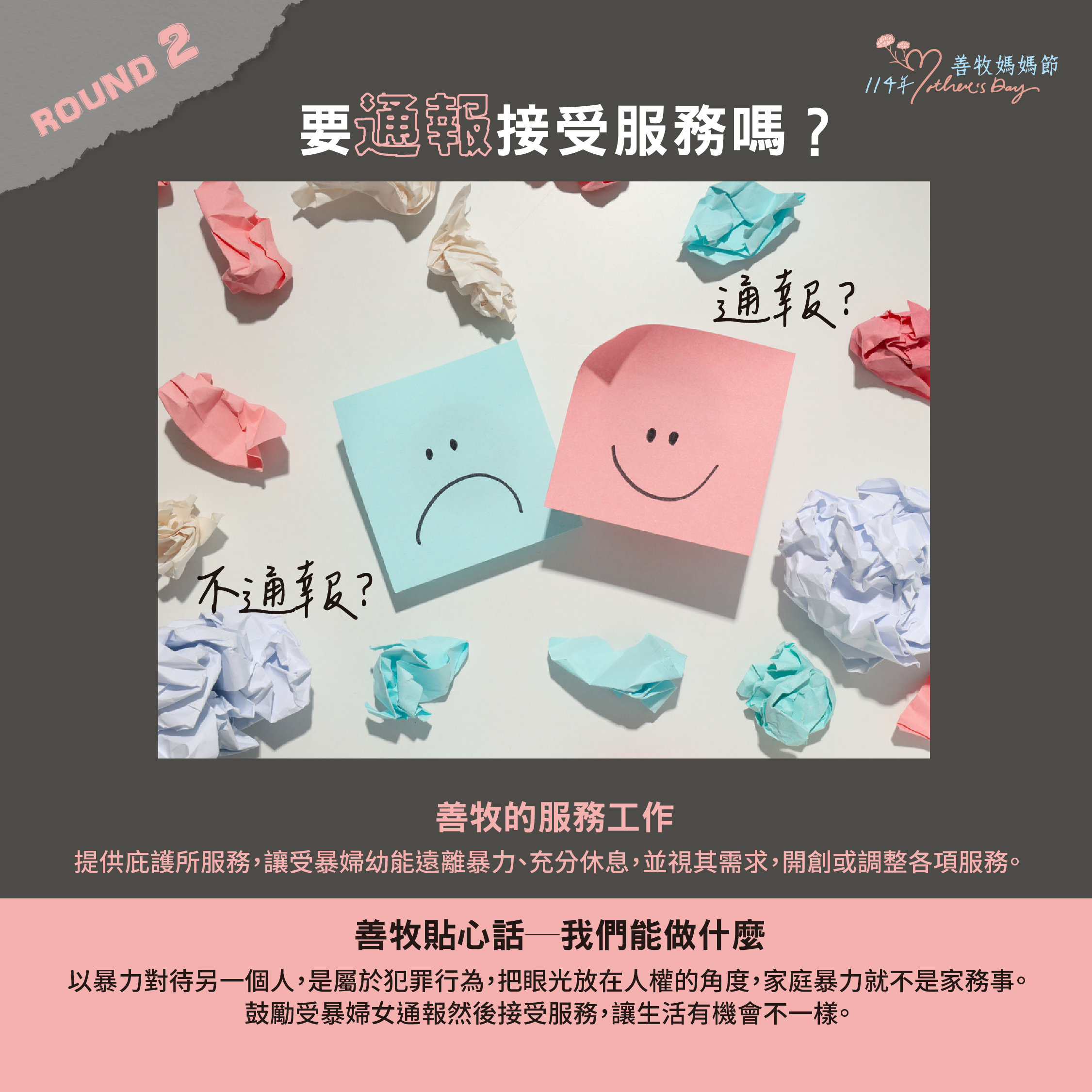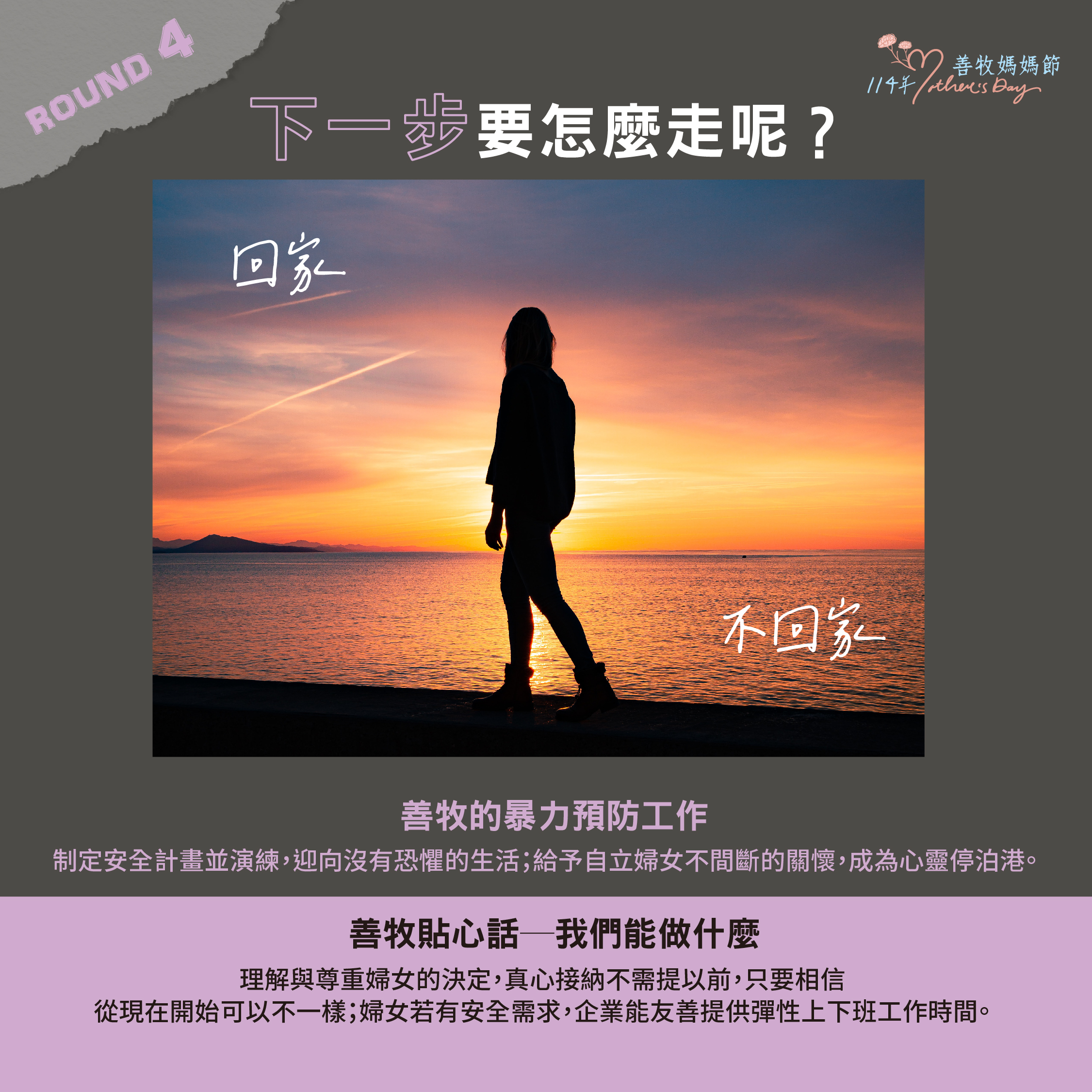根據衛福部統計,110年至112年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數,從53,408人增加至60,856人,上升14%,其中被害人有七成以上是女性。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自民國81年承辦台灣第一所婦幼庇護家園,陪伴許多受暴婦幼長出自己的力量,迄今全台有6家婦幼庇護家園。
善牧的服務包含許多不同境遇的媽媽,從102年起在母親節前後舉辦「善牧媽媽節」,規劃「媽媽就是生命力」攝影展、新住民母親單車活動、收出養家庭紀錄片放映活動……,今年的善牧媽媽節,善牧以多年的庇護經驗,分享服務觀點及看見,期待有更多同理的眼光,給予受暴婦女關懷及支持。
▌跑?不跑?常見離開受暴環境的三大考量
「沒有錢,以後生活會長成什麼樣子?」在新北市經營28年,善牧婦幼庇護家園主任張曉芬分享,經濟最常是婦女猶豫要不要離開受暴環境的首要考量,許多婦女在受暴環境裡面已經很久沒有工作,長時間跟社會脫節,對未來會產生不安全感,因此不容易離開;然而服務中看見,即便有工作的婦女,他們可能在每一次收入進來就一直不斷地支出家計,難有存款;抑或有存款可是全部都被相對人控制,婦女怕拿不到那些錢,想等有十足把握可以拿到錢之後再離開。「經濟」是一個最明顯的顯性樣態,無論有沒有工作,有沒有錢,要脫離受暴環境都還是沒那麼輕而易舉。
第二個最常見的考量是「孩子」。有孩子的婦女,更害怕沒有錢無法養小孩,也擔心爭取不到監護權,這跟經濟的考量環環相扣。婦女想要帶著孩子離開受暴環境,若是經濟能力、照顧的資源都不夠的時候,很難順利脫離相對人,因此有些婦女會想等孩子大一點,帶出來相對比較好照顧,或是不用花那麼多錢了,有的婦女甚至會等孩子成年之後再走。庇護所裡不乏孩子已經17、18歲,甚至20幾歲的,30幾歲的庇護婦女。
相對人的暴力有蠻多比例不只是在婦女身上,也有很多會用在婦女的人際資源,所以第三個考量是「害怕親友遭報復」。相對人為了要讓婦女可以繼續配合他,也會到娘家或是工作場合進行騷擾,造成親友都不敢協助她,婦女也會預期自己離開了,親友會受害而更不敢離開。
張曉芬進一步說明,真的要走到離開暴力環境這一條路是很遠的,因為前面有這麼多的無能為力,談跑跟不跑好像是想離開但離不開,所以選擇先不跑。她也問過有些婦女為什麼不跑,婦女說:「我就可以對付他啊,為什麼要跑」,或是覺得自己說的不被相信,就覺得:「好吧,我就跟他槓上了。」
無論那一種,我們知道每個選擇都是一個困難的選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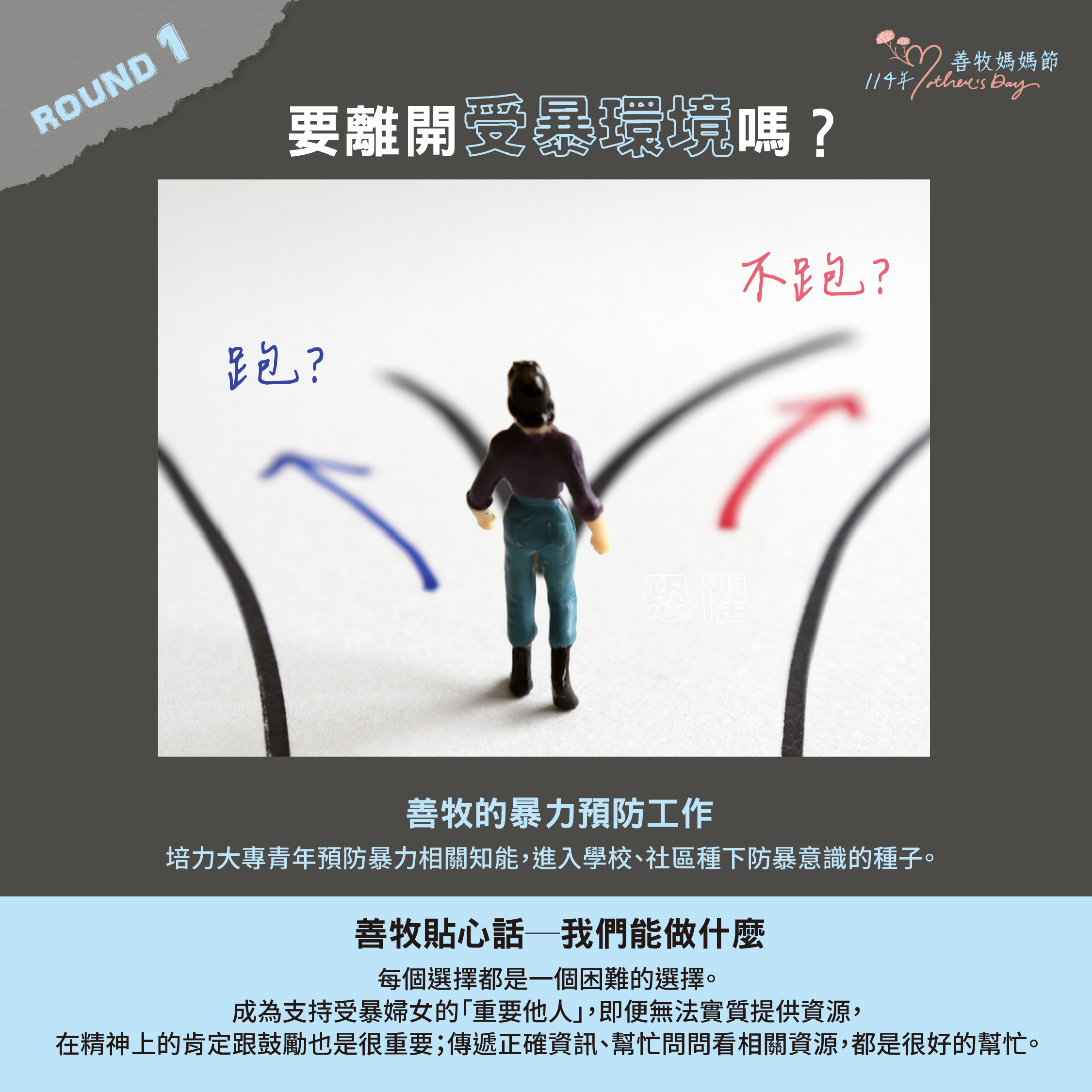
▌通報?不通報?接受服務讓生活有不一樣的可能
家暴是不是家務事呢?有的婦女即便遭遇嚴重肢體暴力,被通報後仍不願意接受服務,覺得這是「我們家的事」,每天打來打去、吵來吵去,生活還是得過,不然還能怎麼樣。張曉芬比喻,像是陷入泥沼一樣,看不到世界其他面貌,自然而然不認為有什麼好改變的,日子過一天算一天,比較難思考到其實是可以離開的,也沒有想過有資源的需求。
張曉芬說,「如果把眼光放在人權的角度,家庭暴力就不是家務事」,那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我相信你是有價值的,值得好好被對待。遏止暴力、遠離暴力,通報並接受服務,是相對比較有機會接觸到多元資源,也是為自己踏出的重要第一步。
專業協助的資源範圍很廣,過往傳統的婦女協助比較著重在安全議題,現在則是聚焦在婦女未來的發展性跟家庭系統等全面性的觀點提供服務,包含:婦女有沒有小孩、未來的生活規劃、建構平穩的生活樣態等,避免再次掉入暴力關係裡面。觸及的議題包含就業、經濟、子女、司法,或是可能長期在家暴環境下造成的憂鬱、精神疾病的需要協助就醫治療,甚至於與社區建立更好的支持網絡、和原生家庭修復關係……,依照婦女需求提供相對應的資源,讓生活有不一樣的可能。
不可諱言地,有鑑於婦女許多考量及錯綜複雜的因素,不是通報的婦女就會接受服務,也不是通報就等於離開暴力環境,即便如此,張曉芬分享,不見得沒有走到最後就是沒有效,她們可能還在中間、還在努力,因為她的心裡已經有不一樣了,那這個不一樣就是可能會在未來發酵,或者是更懂得自己的權益、自己的尊嚴在哪裡,只是可能在現實生活裡還沒有機會去展現的更多。
以暴力對待另一個人,是屬於犯罪行為,當能區辨確實是暴力的狀況,還是得發揮好事者精神,勇於通報,因為,真的有太多人等待這個機會被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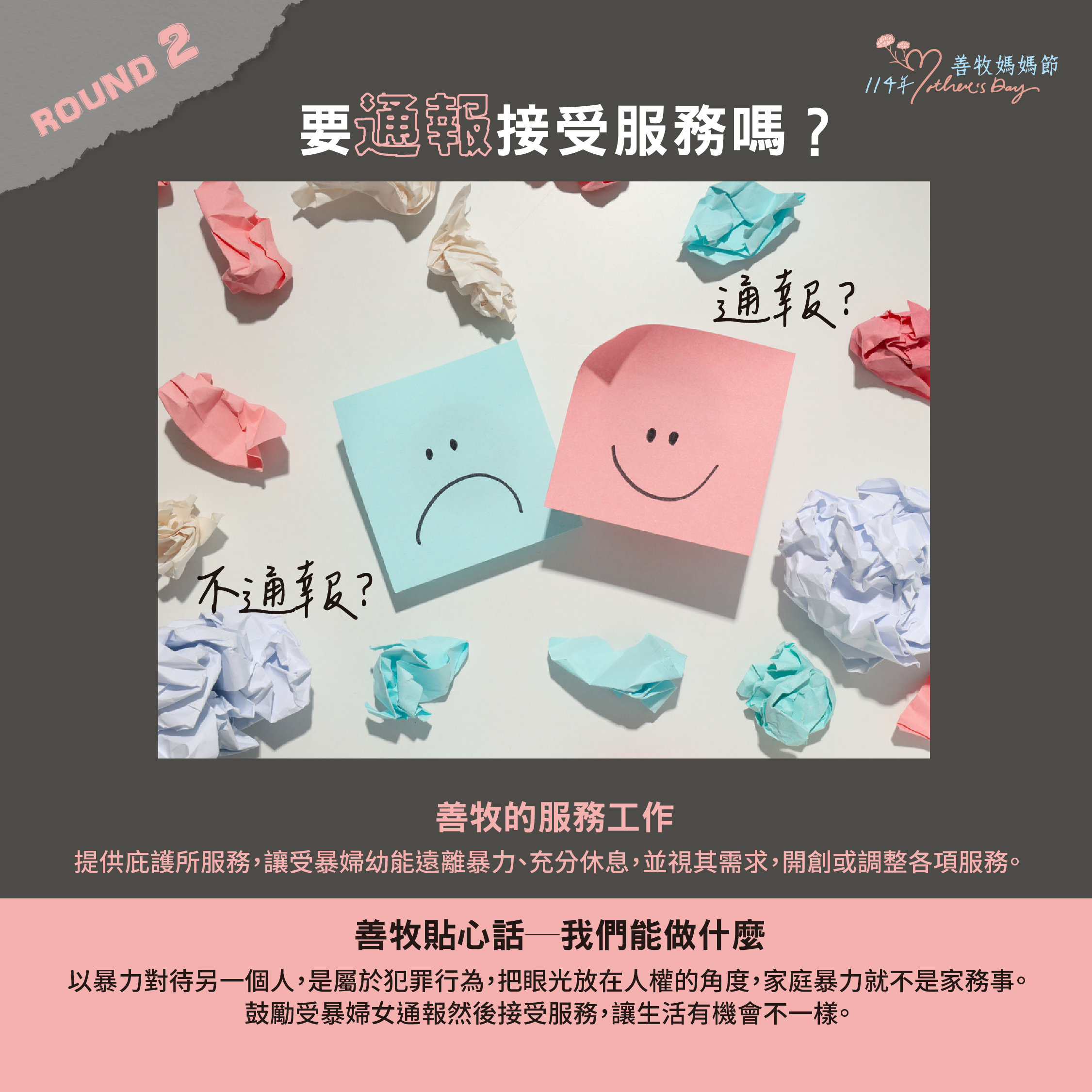
▌我能?我不能?練習看見自己的價值
庇護所是一個隱密、安全,可以讓受暴婦幼遠離暴力、充分休息的地方,會不斷視服務對象的需求,開創或調整各項服務,協助婦女累積面對未來的能量,進而能逐步思索並規劃未來生活。
張曉芬分享,即便是佈置溫暖的庇護家園,對於婦女來說仍是從原來的環境突然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內心充滿不安全感,加上娘家很遠回不去,也可能是不敢回去,完全不知道何去何從,有些婦女晚上在房間自己哭,感到無助;也有些婦女好像讓自己很積極,努力顯示出:我沒事我沒事,但其實心裡亂得不得了。「我們都明白,她們要花很大的力氣讓自己好好的活著。」
所有剛進來的情緒:低落、憂鬱、麻木、隔離、積極……,都會在幾個禮拜後殊途同歸進到另外一個階段,是因為環境比較安全,也比較熟悉了,身心議題開始浮現出來。這段時間婦女的脆弱感會非常強烈,覺得沒有人在乎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誰等等,沒有辦法掌握未來,往往寧可選擇回去她熟悉的關係裡面。
善牧挹注很多種服務,像是生活照顧、親職能力的培養、經濟生活的規劃、醫療健康的協助、就業的安排以及運用社區資源的能力,提供受暴婦女不同階段的支持,並透過團體活動讓婦女重拾對生活的掌控權和選擇權,張曉芬指出,過程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透過「賦能」建構婦女自我價值,讓她們慢慢、慢慢重新看見自己、認識自己,進而回到自己。
「賦能是填充她心裡的狀態,促使內在復原力長出來。」張曉芬進一步說明,人是一個元素,任何的互動都是在給予能量,甚至是一句話、一個動作、一個眼神,從這些日常讓婦女有力量可以支撐,感受到自己是有價值的人。當她們開始喜歡自己、認識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可以承擔什麼、值得什麼,再去思考這段關係要不要留著、要怎麼回應相對人不合理的行為,最後為現階段做一個更好的選擇。

▌返家?不返家?學習安全議題迎向沒有恐懼的生活
善牧的家庭暴力保護庇護服務中,有將近一半以上的婦女選擇返回家庭。在家園期間,善牧努力協助婦女將生理需求及安全需求兩方向鞏固妥當,期待可以移植到婦女返家之後,繼續變成對自己的協助。
生理上若需要用藥、回診,婦女知不知道回診時間,能不能穩定用藥,一定要先建構個人健康管理的責任;安全上,制定安全計畫並演練,討論可能會遇到什麼事,有哪些資源可以因應,並且學習辨識暴力徵兆,降低家暴產生的危機。
然而,對於離開庇護所選擇自立的婦女,除了怎麼樣去預防再回到暴力循環裡,因應壓力的能力非常重要。張曉芬說,生活上一定是已經到一個程度才有辦法自立,所以沒有那麼擔心婦女的生活能力,但從經驗中發現,一旦婦女工作中遇到挫折,或者是有新的親密關係,或是她的相對人再來找她,在各式各樣的壓力當下,心理能量能不能撐住,讓她不再去依附對象,進入一段不好的關係,就成了一個很大的考驗。
善牧利用不斷地與自立婦女來回討論及反思,從前端協助婦女建立健康回應壓力的方式、試著突破負向的關係循環、更細緻辨識暴力危機……,練習對應生活上的各種議題。
與返家婦女相較之下,自立婦女更需要依靠,心理上的依靠,庇護所發展出「暖心賦能計畫」,給予不間斷的關懷,增加她們面對生活上困境的能量,讓家園不只是提供安全休憩的場所,更像是心靈的停泊港。「大部分的自立婦女沒有娘家,那我們就是她們的娘家,你回來就會被我們呵護,這個扎根的存在對婦女們很重要是一個價值感。」張曉芬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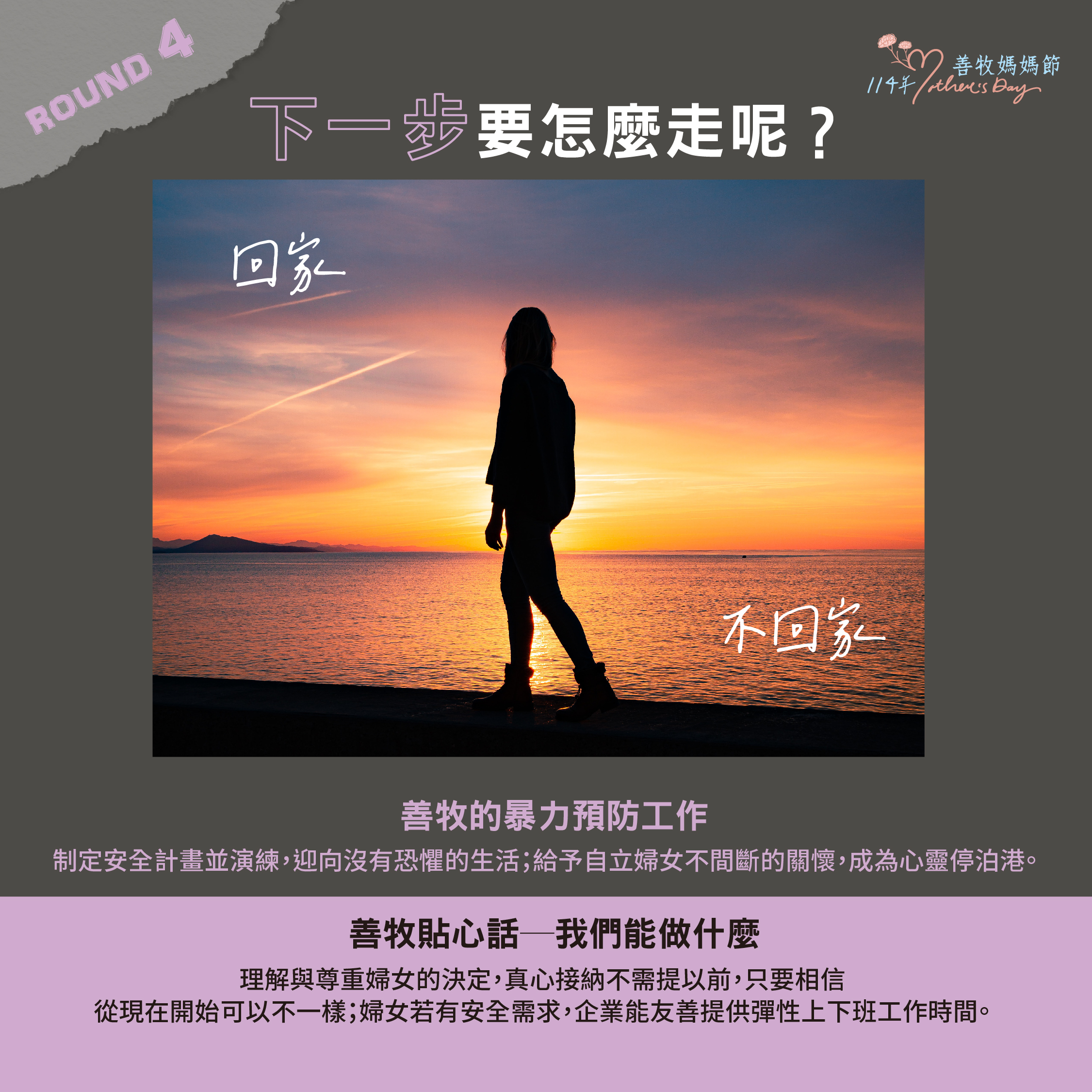
▌感受接納陪伴,重新開始
婦女無論是選擇返家或是決定自立生活,都要面對外在生活壓力,以及內在創傷修復,根據國外研究,平均來說婦女需要來來回回庇護所七次才能夠脫離原本的暴力環境,足見改變並非容易的事。
對於多次進入庇護所的婦女,張曉芬以正向眼光看待婦女反覆的選擇,「生活中要吃什麼不吃什麼,不也都一樣反反覆覆做選擇嗎?小的事情都可以這樣,更何況是人生上的事情、關係上的事情本來就不容易,」重要的是,婦女每一次進入庇護所都是不同的,也許尋求安置的間隔時間拉長了,也許是她們為自己又多做些準備了,也許是在庇護所復原的時間更短了……「我們相信,只要婦女願意選擇,就再有一次機會,都很好。」
張曉芬提醒,對於婦女開始啟動想要為自己做另外一個選擇的時候,也許無法給予太多資源,只要好好鼓勵她、肯定她的勇敢,就能帶動她的自我價值;對於走向自立重新開始的婦女,真心地去接納她們,不需要提太多以前的故事,只要相信從現在開始可以不一樣。
我們都是每個人的重要他人,在受暴婦女的分岔路口,可以提供正確資訊、可以提供「你是有價值」的信念,協助她們在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多增加一股支持力量。
114年的善牧媽媽節,善牧也邀請民眾支持受暴婦幼庇護工作,協助更多婦女找到自己,走出暴力環境。